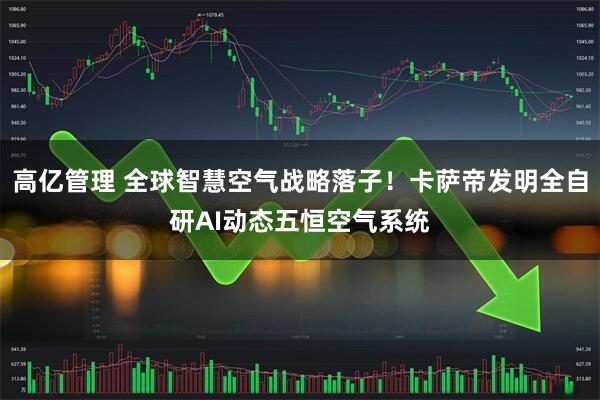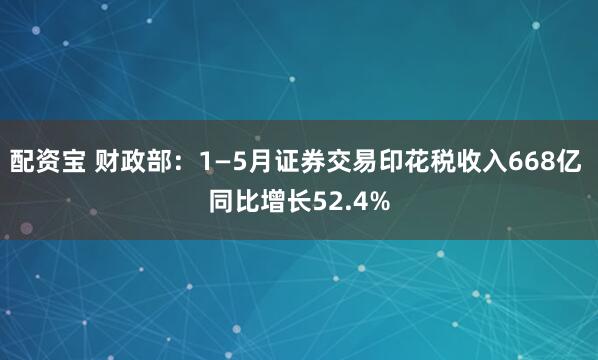长久以来信汇网,长征题材文学的叙事重心多聚焦于“英雄谱系”——指挥若定的将领、冲锋陷阵的战士、舍生取义的烈士,这些“高大全”的英雄形象,以超凡的意志与壮举构建起长征精神的“经典叙事”。然而,长征的胜利从来不是“英雄的独角戏”,而是无数普通人用坚守、善意与行动共同托举的“集体史诗”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莆田作家,张元坤深耕文学领域多年,其创作始终浸润着壶兰大地的文化肌理,既以本土经验为锚点,又以开放视野观照时代精神(《壶兰诗影》中“一身正气贯长虹”的传统智德推崇便是明证)。他的《断刃成锋:红军伤兵绝地突围》恰恰跳出了“英雄叙事”的惯性框架,将镜头对准伤兵、村民、儿童等“非英雄群体”,通过刻画他们的犹豫与坚定、恐惧与勇敢、朴素与真诚,还原出长征最本真的“人民底色”——长征不仅是“军队的远征”,更是“人民的远征”;长征精神不仅是“英雄的品格”,更是“人民的精神”。
一、作家底色:莆田文化基因与“共生”叙事的深层联结
张元坤的创作始终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。作为莆田籍作家,他深谙壶兰文化中“邻里互助”“守望相助”的乡土伦理,这种对“共生关系”的敏锐感知,成为其解构长征英雄叙事的重要精神资源。在《壶兰诗影》中,他便以“共生”为核心命题展开哲思,通过“智如朗月照古今,德似春风拂万物”等诗句,将传统智德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诉求相联结。这种创作基因自然延续到《断刃成锋》中,使其跳出了“英雄拯救人民”的单向叙事,转而构建“军民共生、双向支撑”的叙事图景。
展开剩余83%同时,作为“东南新视”创始人,张元坤兼具“地域文化深耕者”与“时代观察者”的双重身份。他既善于从莆田乡土社会的“日常伦理”中提炼创作素材——如《断刃成锋》中村民“凑粮缝衣”的细节,便可见莆田民间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”的生活原型;又能以宏观视野把握时代对“普通人叙事”的需求。这种“扎根地域却不囿于地域”的特质,让他笔下的“非英雄群像”既带着乡土的温度,又具备跨越时空的普遍共鸣。
二、解构“英雄符号”:让“非英雄”从“背景板”走向“叙事核心”
传统长征文学中,“非英雄群体”往往是“英雄叙事”的“背景板”——村民是“送粮送衣的集体符号”,儿童是“传递情报的工具人”信汇网,他们的存在只为衬托英雄的伟大,却鲜有属于自己的“人性细节”与“选择逻辑”。《断刃成锋》则彻底颠覆了这种叙事定位,让“非英雄群体”成为绝对的“叙事核心”,他们不再是“符号化的配角”,而是有血有肉、有挣扎有坚守的“生活主角”。
小说聚焦的“非英雄群像”,可分为三类:一是“受伤的普通人”——因重伤掉队的红军伤兵。赵刚腿伤严重,曾因“怕拖累大家”想留在山林;孙明手臂被子弹打穿,无法持枪时沮丧地说“我成了废人”;张勇年纪最小,夜里疼得哭出声,却仍攥着半块干粮说“要留给更需要的人”。他们不是“不怕疼、不怕死”的英雄,而是会疼、会怕、会沮丧的普通人,他们的“坚守”不是源于“英雄使命”,而是源于“归队的信念”与“不辜负村民帮助的愧疚”。
二是“犹豫的守护者”——塘家庄的村民。教书先生赵有为最初掩护伤兵时,“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既怕被保安团发现连累妻儿,又不忍心把受伤的人推出去”;村民李婶送粮时曾犹豫“自家粮食都不够吃,分给红军,孩子要饿肚子”;老猎人起初不愿掺和,“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直到看到伤兵们忍着剧痛帮村民修补漏雨的屋顶,才主动上山教他们识别野菜与陷阱。他们的“帮助”不是源于“革命觉悟”,而是源于“对弱者的同情”“对善意的回馈”“对家园的守护”,充满了普通人的纠结与真实。
三是“懵懂的传承者”——村里的儿童。小柱子送干粮时遇到保安团,“吓得腿发软,差点把篮子掉在地上,却还是下意识把装着窝头的油纸往身后藏”;小花看到林晓的腿伤,“一边哭一边把兜里的糖塞过去,说‘吃了糖就不疼了’”;小石头不会讲革命道理,却每天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放哨,“看到穿灰制服的人就摇响铜铃,冻得手通红也不离开”。他们的“行动”不是源于“革命信仰”,而是源于“对红军叔叔的亲近”“对‘好人’的朴素认知”,带着孩童特有的稚嫩与纯粹。
这些“非英雄”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以“普通人的姿态”占据了叙事的核心。张元坤没有刻意拔高他们,反而不回避他们的弱点——犹豫、恐惧、自私的念头,正是这些“不完美”,让“非英雄群像”摆脱了“符号化”的桎梏,成为长征历史中“人民”的真实缩影,也让长征的“人民底色”有了最鲜活的载体。这种创作手法,与他在《律中寄潮》中“记录现实肌理、回应精神困惑”的创作追求一脉相承,都是对“真实人性”的深度挖掘。
三、聚焦“日常选择”:在“细微行动”中彰显人民的“精神力量”信汇网
传统长征文学多以“宏大事件”彰显精神——战役的胜利、战略的转折、英雄的牺牲,这些“大事件”固然震撼,却难以体现“人民”在长征中的具体价值。《断刃成锋》则将叙事焦点从“宏大事件”转向“日常选择”,通过“送一碗粥、缝一件衣、放一次哨”等细微行动,展现“非英雄群体”如何以“平凡之力”支撑起长征的“人民根基”。
这些“日常选择”,藏着最朴素的善意。赵有为的妻子每天清晨都会把熬好的红薯粥装进瓦罐,裹上棉袄揣在怀里,绕远路送到山林——“瓦罐外壁凝着水珠,她怕粥凉了,走得飞快,额头上渗着汗”;村里的妇女们凑在一起,把自家的旧棉衣拆了重缝,给伤兵改出合身的小棉袄,“针脚歪歪扭扭,却缝得格外密实,里子还缝了个小口袋,能装随身的药”。这些细节恰是张元坤对莆田乡土“烟火气”的文学转化,他将壶兰大地“邻里互赠吃食、互助缝补”的日常场景,植入长征叙事中,让“人民的善意”不再是抽象概念,而是可触摸的生活细节。
这些“日常选择”,藏着最勇敢的坚守。当保安团封山搜查,赵有为被抓去盘问,“被打得嘴角流血,却还是咬着牙说‘没见过陌生人’”;李婶看到保安团要搜山,故意把鸡赶到山路上,“一边追鸡一边喊‘谁家的鸡跑了’,拖延敌人的时间”。这种“普通人的勇敢”,与张元坤在诗集中歌颂的“一身正气贯长虹”形成呼应——他不将“正气”局限于英雄壮举,而是将其解构为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“不退缩”,这种解读让传统美德有了当代落点。
这些“日常选择”,藏着最坚定的信任。村民们愿意把仅有的粮食分给伤兵,是因为“看到伤兵们不抢不夺,还帮着村民耕地、修补屋顶”;伤兵们愿意相信村民的掩护,是因为“赵有为把妻儿托付给邻居,自己留下来陪着他们躲山洞”。这种“双向信任”,正是张元坤“共生”哲思的文学表达,他通过长征中的军民互动,诠释了“共生不是单向索取,而是双向奔赴”的深刻内涵,这与他在《壶兰诗影》中对“原子化社会孤独症候”的反思形成鲜明对照。
四、还原“人民底色”:重新定义长征精神的“集体内涵”
传统长征叙事多将长征精神解读为“英雄的个体品格”——如“坚韧不拔”“无私奉献”“英勇无畏”,这种解读固然有其价值,却忽略了长征精神的“集体内涵”:长征精神是“红军与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”,是“个体坚守与集体支撑的共生体”。《断刃成锋》通过“非英雄群像”的刻画,重新定义了长征精神的“集体内涵”,也让长征的“人民底色”有了更深层的价值指向。
在小说中,长征精神的“集体内涵”,体现在“军民共生”的相互支撑里。红军与人民不是“单向的支援关系”,而是“双向的共生关系”:伤兵们保护村民抵御保安团的欺压(如护村战中,孙明忍着手臂疼痛开枪击退敌人),村民们则为伤兵提供生存的保障(粮食、草药、藏身之处);红军将“平等、正义”的理念传递给村民(李强给孩子们讲“不被欺负的日子”),村民则将“乡土伦理”(同情弱者、守护家园)融入革命精神。这种叙事,正是张元坤将莆田“邻里共生”文化升华为普遍精神命题的创作实践——他从本土经验出发,却超越了地域局限,让“共生精神”成为解读长征的新钥匙。
同时,长征精神的“集体内涵”,体现在“普通人的坚守”里。赵有为“在恐惧中仍选择掩护”,是对“正义”的坚守;孙明“在沮丧中仍想归队”,是对“信念”的坚守;李婶“在自私的念头里仍选择送粮”,是对“善意”的坚守。这些“普通人的坚守”,没有英雄的“壮烈感”,却有“水滴石穿”的力量——它们证明:长征精神不是“英雄的专属”,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的品质。这一创作理念,与张元坤在《律中寄潮》中“为时代提供精神解药”的追求高度一致,他始终相信,文学应“为大众立心”,让普通人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的精神镜像。
结语
当莆田作家张元坤带着壶兰文化的“共生”基因与“真实叙事”理念,跳出“英雄叙事”聚焦“非英雄群像”时,他不仅为长征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视角,更完成了对长征“人民底色”的深度还原。从《壶兰诗影》对地域精神的挖掘,到《断刃成锋》对长征叙事的重构,张元坤始终坚守“扎根现实、观照人性”的创作初心——他让“人民”重新回到长征叙事的中心,让读者明白:长征不是遥不可及的“英雄传说”,而是与每个普通人都相关的“集体记忆”;长征精神的伟大,不仅在于英雄们的“超凡壮举”,更在于人民们的“平凡坚守”。
这部作品的价值,在于它让“人民底色”成为长征最鲜明的标识信汇网,也让张元坤的创作理念得到印证:优秀的红色文学,既需要扎根历史的厚度,也需要带着地域文化的温度;既需要观照时代的广度,更需要触摸人性的深度。当越来越多的读者从《断刃成锋》的“非英雄群像”中读懂“人民”的意义,长征精神便能真正融入当代生活,成为滋养心灵、凝聚力量的“精神养分”。
发布于:福建省宝龙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